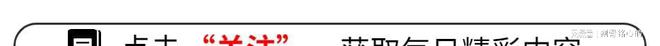50年前,《驱魔人》上映。
当时华纳并不看好这部恐怖片,加上影片试映口碑也不算好,华纳只准备小范围上映影片。
令人没想到的是,影片上映后,成为了现象,大批影迷在寒冬里排队等着看电影。
最终,《驱魔人》收获了4.41亿美元。

《驱魔人》定义了恐怖片的类型——一如《德古拉》和《科学怪人》——推动了恐怖片的发展。
在漫长的岁月里,驱魔类型的影片越来越多。
除了《驱魔人》及其衍生的各种续集、外传和前传,温子仁也依靠此类型开发了《潜伏》和《宅混》,成为了新时代里恐怖片的标杆。
甚至在2023年,罗素·克劳还出演了《教皇的驱魔人》。

50年后,影片导演威廉·弗莱德金逝世,华纳官宣将要开发一部直接承袭于原作的续集,并将打造一个完整的三部曲。
故事将依照弗莱德金所开发出来的路线,讲述另一起发生在当代社会的驱魔事件。
《驱魔人》究竟有什么魔力,如此令人恋恋不忘?

驱魔人的真相
POST WAVE FILM
魔鬼附身这件事,听起来荒诞。
但编剧布雷迪却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戏剧化”地处理整个事件。
第一次接触驱魔是在1949年,布雷迪大三,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了马里兰州的一个驱魔新闻。
在当时的报道中,化名罗兰·罗伊的14岁男孩,企图用“亡灵游戏”来召回和他最亲近的姨妈。
但他没有召回姨妈,反而惹上了恶魔。

几天之后,罗伊开始显现被“恶魔附身”的情况。
他说自己的床不断地摇晃,身上出现了大量的符号;尿失禁、痉挛、呕吐接踵而至;他甚至无师自通了几门上古中东语。
罗伊的父母本是无神论者,可求医无门,只能诉诸于神明的力量。

在经过请示梵蒂冈、提交证据以及一系列例行流程后,保登神父对罗伊展开了驱魔仪式,最终成功保住了罗伊的性命。
一年之后,这个故事被写成了《神父解救着魔男童》(Priest Frees Mt. Rainier Boy Reported Held in Devil's Grip)登在了《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
而根据梵蒂冈的要求,1948年的这次驱魔,没有被公开。
相关的全部档案,包括保登神父的录音和录像,都被封存在了梵蒂冈的档案馆。

换而言之,《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只是一个见闻录,可信度存疑。
但即便如此,布雷迪还是对此事件撰写了一篇研究性的论文,后来这篇论文也刊登在了《华盛顿邮报》上。
进入大众视野的驱魔,成了教徒们狂欢的理由。
每一年,教徒们都会在罗伊的旧宅附近举办“驱魔表演”,以彰显神明的伟岸。
这个习惯延续至今。

1970年,经过9个月的创作,布雷迪半虚构半纪实的作品《驱魔人》出版。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这本书被卖掉了1300万册。
2年后,这个故事被拍成了《驱魔人》。
此后,整个美国宗教界为此展开争吵。

有神父称赞影片对耶稣会信徒表现出的“苦痛和挣扎,相互之间兄弟般的情谊,默默地帮助他人的品质”所打动。
也有神父认为这是部邪恶的影片,比利·格拉姆曾经在布道中说:“影片的每一格胶片,都被恶魔附体了”。

1978年,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新一任教皇。
他撤掉了官方驱魔人,教廷日渐保守,不少主教不得不自己选择驱魔人。
到了1980年代,驱魔人已经不再“驱魔”,而是成为“心理治疗师”,帮助瘾君子和人格分裂的教徒。
恐怖大蔓延
POST WAVE FILM
影片中,导演弗莱德金不断混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来营造恐怖效果。
在看完样片后,华纳兄弟对这种超现实的风格没有把握,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小范围内上映了影片。
始料未及的是,影片经过观众的口口相传,获得了巨大的市场。
剧院外始终有观众排着队,等着影片上映。

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驱魔人》小说的拥趸,毕竟这部小说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呆了一年之久;另一部分人是不怕死的观众,以身试法,就要看看电影有多恐怖。
很多观众被吓出了严重的生理反应,他们呕吐、晕厥,甚至被吓出了心脏病。
洛杉矶的一位院线经理统计,几乎每个场次都有4例晕厥和6例呕吐;一个英国男孩看完电影后,发了癫痫,第二天死去;一个男子确信自己被魔鬼附身,在教堂让神父驱魔一夜。

面对如此大胆肆意的影片,英国下了“禁映令”,这项禁令直到1999年才被解除。
评价恐怖片的黄金标准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足够恐怖。
在这种态势下,当年影评人的口诛笔伐诟病咒骂,都显得势单力薄。
《纽约时报》当时说,“影片用宗教做噱头,用感官刺激和性来挣钱”。
曾因批评《音乐之声》而被解雇的宝琳·凯尔说:“《驱魔人》最严重的缺陷是没有任何目的和象征意义”。

诸多影评人看来,“魔鬼附身”没有带来探索母女关系、代沟、人性沟通的价值,只是“一本正经的专攻下三路”。
实际并非如此。
1973年,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身陷泥潭。
很多参与了越战,充满愧疚的父母,回到了美国。
他们所面对的是自己满口污言秽语,甚至还染上了毒品的孩子。
社会矛盾集中到了两代人的代沟之中。

老一辈看着反动的年轻人,束手无策;年轻人无所不用其极,让长辈蒙羞。
于是,石墙暴动、嬉皮士运动,都在这一个时间段大爆发。
所以,影片的宣传语这样写:“驱除在越战时期充满愧疚和责任感父母困惑的文化仪式。”

这是自满的影评人对电影又一次误读,凯尔希望天主教徒们不要“坐视他们的信仰沦为一场恐惧秀”。
可“作秀”却是制片方“有意为之”的操作,有组织的宗教团体,猎奇性的驱魔仪式,都大大刺激了观众。
在美国,不管他是不是教徒,他们所知的有关宗教的大多数事“都来自于电影”。
这种主流传播途径,被教会视为“穷人的圣经”,也被影评人视为“能想象到的最低级品位。

凯尔终究还是错付了。
如果她能活着看到驱魔题材,在新世纪里出现了这么多东施效颦之作。
那她就会明白,自己那“关于宗教奇迹毫无感觉的电影”的批判,写得太早。
中国也有驱魔故事
POST WAVE FILM
驱魔并不是国外的专利。
中国的民间故事,也有着丰富的驱魔题材。
而且,中国民间故事里,这种降魔的法术,总是带有夸张的神秘主义色彩,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倩女幽魂》系列。

《倩女幽魂》的故事出自蒲松龄的《聊斋》。
在这本书里,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四种“驱魔人”:半仙、豪侠、素人,其中最多的还是僧道。
僧人属于佛教,道人属于道教。
对比西方的驱魔人来说,都有点类似于神职。
比如《画皮》原著里,有一个青帝庙道士,就是个用法器的高手,他前前后后用了蝇拂、木剑和葫芦,才将邪魔收服。
只不过在电影改编的时候,这个故事变得更现代化了,跟宗教疏远了。

《画皮2》剧照
还有一个故事叫《焦螟》。
它说的是一个叫董默庵家的官员,家里出现了一个狐妖,不胜其烦的他,找来了关东道士焦螟,求他除魔。
焦螟先画了一个符,没有用;后筑坛作法,也没有用。
最后,他使出了戟指咒,终于除掉了狐妖。
而在焦螟除妖之后,这家人开始对道教倍加赞誉,也有了敬畏心理。

西方用十字架、念《圣经》,东方画道符、念咒语。
这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驱魔人》的故事里,上帝从始至终都是坚定的后盾。
而在《聊斋》中,神仙往往是隐匿在驱魔事件后面,那个不做声的角色。
比如《青蛇》里,法海在施展法术跟白娘子大战时,经常会先说一句“大威天龙”。

这个咒语的完整念法其实是:“大威天龙,世尊地藏,般若诸佛,般若巴嘛空。”
你看,这妥妥就是一个跟地藏菩萨相关的法术。
这背后隐藏的,其实就是对佛教权威的借用。
也就是说,《青蛇》里法海的这个做法,跟《驱魔人》里牧师手拿经书、撒圣水的操作,在底层逻辑上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在加固和信仰的存在。
只不过在电影的叙述手法里,它们变得更戏剧化罢了。
作者丨云起君
放大头像看我眼神
编辑丨毛头 排版丨lmx
媒体统筹丨佐爷灵魂贩卖馆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豆瓣及网络,
若有侵权请主动联系我们。」
近 期 好 课
好课 | 故事片创作工作坊
好课 | 带你写出电影剧本
⬆️ 关 注 【 后 浪 电 影 学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