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叶维杰、毛克疾】
9月10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正式在印首都新德里闭幕。G20峰会期间,印总理莫迪可谓大放异彩,不仅推动各成员国达成联合公报,更是先后与美、法发布联合声明,面子里子挣了个盆满钵满,足足“过把瘾”。
然而,在印G20“大获全胜”的背后尤有一件值得关注,且正在印国内舆论场发酵之事,那便是“印度改名”。改名一事其实并不复杂:以莫迪为首的印人党政府企图以国家的印地语名“巴拉特”(BHARAT,又译婆罗多)取代其英文名“印度”(INDIA),达到更彻底实现“本土化”的目的。
事实上,印度国名归属问题这一“国本”之争此前便已上演过。英属印度时期,南亚次大陆居民普遍以“Bharat”“India”“Hindustan”三词称呼彼时的印度(包括现在的印度、缅甸、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部分)。独立期间,印社会各界主要围绕以上三词就国名采用一事展开激烈辩论。“Hindustan”因其“印度教徒之地”的含义被率先排除,后坚定世俗主义路线的尼赫鲁出于兼顾国内其他宗教信仰者的考量态度,在巴拉特和印度这两大热点名称中采取了折中做法,从而便有了印度宪法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印度,即是巴拉特,应是一个联邦。(India, that is Bharat, shall be a Union of States.)”这也意味着,印度和巴拉特是可以互换着使用的。
然而,问题是,尽管宪法对国名已有定论,印社会各界仍广泛使用“印度”“巴拉特”“印度斯坦”这三个名称,同时学界亦基本达成“根据语言环境”灵活使用上述名称的共识。这一现象表明,印度有关国名的争论从未停止。
其中,部分强势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要求将宪法第一句的“印度”“巴拉特”调换位置,改为“Bharat, that is India, shall be a Union of States”。更有甚者直接要求删除“印度”,仅保留“巴拉特”。例如,2004年4月,印度社会党(SP)提议在宪法仅采用“巴拉特”之名,以此遏制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所助长的文化堕落,以保护印度国家安全。但毫无例外,此类举措均遭到印最高法院的反对。
那么,“巴拉特”一词究竟有何魅力,竟让莫迪政府直接借G20峰会之机“先斩后奏”,不惜采取先在国际活动上更改国名以营造某种既定事实,之后再在国内完成相应程序的“先外后内”的打法推动变革?

印度总理莫迪在G20峰会发表讲话,座签上使用的称呼是“BHARAT” 。图自欧洲通讯社
“印度”和“巴拉特”
首先,应从“印度”“巴拉特”二词的由来及意义说起。印度斯坦由Hindu发展而来,公元3世纪时被波斯用以指代印度河流域地区,后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下被赋予政治、宗教意义。而印度(INDIA)的名称起源于“Sindhu”一词的音译。Sindhu为印度河的名称,记载于现存最古老的印欧语文本《梨俱吠陀》中(创作于公元前1700-1100年)。后因发音系统的差异,彼时同印度接触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将“S”读成“H”,将印度河流域附近的地方(如今巴基斯坦信德省)统称为Hindu。
公元前486年,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用“Hidush”称呼被其征服的“印度土地”。后经多方辗转发展,“印度”被希腊人称为Ἰνδία(Indía)。之后古英语(公元5世纪中叶至12世纪中叶之间)通过吸收希腊术语,发展出India这一词汇。再后来该词受法语影响,演化为Ynde或Inde取代,被用于早期现代英语(15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650年)。自17世纪起,随着英国人逐步在南亚次大陆扩张势力,India被重新使用,用以指代当时的南亚次大陆。
直到英国殖民者最终完成英属印度版图的扩张,“印度”这一名称被正式赋予地理、政治意义。由此看,India这一名词起源于印度河(Sindhu),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阿拉伯、希腊、法国、英国等不同文化的影响,最终成为涵盖如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集群的地理名称。
而“巴拉特”则为纯粹的梵语、印地语词汇,英文转写为Bharat,在印地语语境下等同于“印度”。该词最早可追溯至早期的印度教经典文献,具有多重含义,既可以指古印度的君王、婆罗多部族,也可以指代南亚次大陆。在《往世书》等早期梵文文本中,巴拉特指代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社会制度盛行的超区域和次大陆地区,存在空间和社会层面的封闭性。
按文本释义,巴拉特是一个有着天然边界的区域,广义上来说指代海洋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所有区域,同时受特定社会秩序所约束,但并未指向任何一个边界明晰的地域。因此,长期以来,巴拉特更多指代特定空间下的社会秩序,而非某一地理、政治实体。直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知识分子才赋予巴拉特全新内涵,同时将其政治化,即宣称巴拉特是印度的“古名”。
通过对比可得出,“India”所指几乎囊括整个南亚次大陆,是一个完整的地理、政治实体,具有空间和政治的统一性,而“Bharat”主要指代一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基于此,反对改名人士宣称的“印度这一名字更具有品牌价值”这一说法具备相当张力。但对于注重印度教民族主义事业的印人党政府来说,“巴拉特”无疑更加有助于其开展民族事业。印人党官方人士对“改名”一事的回答不全面但足够清晰,“巴拉特是本土文化的象征,可摆脱殖民主义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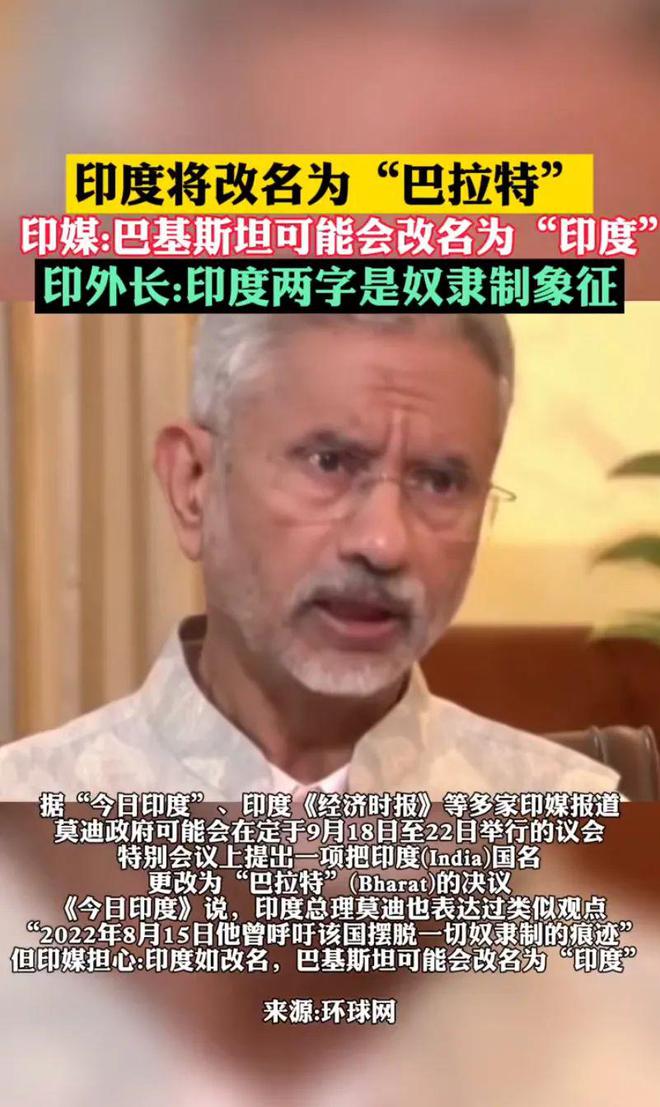
印度外长回应改名争议 视频截图
改名原因
其次,“改名”和印近期各党派的政治动态有关。从时间顺序上来看,莫迪政府借G20突然提出“改名”有一定的紧迫以及局限性。但若是将其同印内部政治动态结合,便相当合理了。
2023年7月,众反对党宣布结成新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n National Developmental Inclusive Alliance,INDIA)。在名头上,反对党联盟就独占了个“印度”,这自然不能为向来在政治斗争中久居上风的印人党所接受。自此,印人党便频繁提及“改名”一事,又恰逢G20峰会这一绝佳时机。9月5日,印总统穆尔穆在致G20领导人的晚宴邀请函上以“巴拉特总统”而非“印度总统”的名义称呼自己。9月9-10日,莫迪在G20峰会上使用“BHARAT”的铭牌而非“INDIA”,一举将“改名”事件推上高潮。
自此,在国际上的“印巴之争”有所缓和的背景下,印度在其国内又人为地制造了一起“印巴之争”,似乎不存在任何缓和余地。
更有意思的是,部分分析人士甚至建议巴基斯坦改名为“印度”,理由是“India”最初所指代的印度河流域地区正是如今巴基斯坦所在。基于此,“印巴之争”变为“巴印之争”亦有可能。
最后,还应结合莫迪的政治野心。自2014年上任伊始,莫迪便致力于推动印地语成为国语和促进基于民族之上的国族认同,即为“国语进程”和“国族再造”。然而,印度《宪法》规定的22种印官方语言中无任何一种语言被赋予国语地位。发展至今,全印将印地语作为第一、第二或是第三语言的人数不足50%, 70多年前尼赫鲁政府所做不到的事,想必莫迪政府如今也很难实现——语种多样的南印首先便不会同意,更不用说反对党了。
莫迪政府大张旗鼓营造“改名”一事或许正是基于此考量,即通过更名在国民心中种下带有民族归属感的心理暗示,之后为印地语徐徐图谋“国语地位”一事。
同时,莫迪推动改名的准备充足。据印媒披露,莫迪政府9月18-22日拟举行议会特别会议,其中最为关键的两大议程便是“改名”和“同时举行人民院选举和邦级选举(一国一选)”。莫迪政府对后者的解释是削减选举预算、节省时间,但其增加选举胜算的意图不言自明。
另外,尽管“一国一选”的通过难度较大,但仍可反映莫迪政府正尽可能消除“改名”带来的不利影响,以期实现连任。这进一步反映莫迪政府以选举利益为中心的目的导向,及其所谓的印度文明国家理念——不过是一种狭义的、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

当地时间8月31日,反对党组成的“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在孟买举行第三次会议。图自印媒
未来如何?
改名一事,说小不小,说大不大。荷兰(Netherlands,原为Holland)、斯里兰卡(Sri Lanka,原为Ceylon)、泰国(Thailand,原为Siam暹罗)、缅甸(Myanmar,原为Burma)等国先后均更改了其国名。印度国内的孟买(Mumbai,原为Bombay)、金奈(Chennai,原为Madras)、班加罗尔(Bengaluru,原为Bangalore)、加尔各答(Kolkata,原为Calcutta)、科钦(Kochi,原为Cochin)等城市亦先后抛弃其具有殖民色彩的名称。
但对绝大多数印度教徒而言,“印度”仅是一个领土概念,而“巴拉特”的含义则不止于此。印民众赞颂国家时通常说“巴拉特母亲万岁”(Bharat Mata ki Jai),而不是“印度万岁”(India ki Jai)。因此,将国名改为“婆罗多”更能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
问题是,莫迪若要成功推动国名更改,需议会上下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数同意。但印人党近期在南印卡纳塔克邦选举的颓势表现(以66比135负于国大党)证实,印人党鼓吹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存在局限性,即所谓主义无法取代发展,情感牌无法填补物质空缺。
但无论成功与否,印人党政府将“巴拉特”置于“印度”之上已是不争事实,必然进一步加剧以印人党为首的“巴派”阵营和以反对党联盟为主的“印派”阵营的二分对立。也注定印度朝着逆多元化、狭义的文明构建道路上越行越远。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